任何政治经济学模型如果不重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就有可能流于言之无物,失之偏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利益集团就是政治结果的最终决定因素。在这里,我将挑战一种观点:在利益集团和结果之间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对应关系取决于许多隐含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与政治行为人对如下几个方面所持有的观念相关:(1)最大化目标的性质;(2)世界是如何运行的;(3)他们追求更大利益而采用的工具集。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既有可能被操纵,也有可能被创新,成为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正如我将展示的,实际上,政治领域中的游说投资和政策创新非常类似于技术发明活动(经济学家通常将之内生化)。只要我们认识到观念的易变性,就可以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决策权,于是,就会产生更多可能的结果。
虽然所有的经济学模型都有隐含假设,但是,我将论证: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正确认识观念在利益形成和利益追求中的作用,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考虑观念因素,我们便能更令人信服地解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变革。这有助于消除政策分析(应该做什么)与政治经济学(实际发生了什么)之间的尖锐分歧。它还解释了现实中经常出现的异常现象:在实践中,许多改革最后反而使原本阻止改革的精英们受益。
首先,我对观念融入政治经济学模型的方式(往往以隐含方式)进行了分类。其次,我将重点关注那些力求解释经济低效率的模型,并论证这些模型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既得利益本身,也取决于精英们对可行策略所持有的观念。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关于政策或政策创新(policy entrepreneurship)的新观念会对均衡结果产生独立的影响,即使在政治权力架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最后,我将论述新观念的来源。 明确观念的作用 任何理性选择模型都基于个体决策者有意识的行为。通常,假定个体解决一个明确的最优化问题即构成行为。在这个最优化过程中,必须设定至少三个要件:(1)目标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2)一系列约束条件(如预算约束);(3)一系列选择变量(如可选择的消费数量)。基于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这一框架应用于政治领域。政治行为人(投票人、说客、精英、国会议员)被描绘成解决最优化问题的理性个体。这意味着:(1)他们通过定义消费、租金或政治收益来最大化效用函数;(2)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施加的约束条件内采取行动;(3)他们选择一系列行为(在模型中可能包括选举、政治捐款、叛乱、镇压等),来实现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最大化。例如,商业游说集团为获得关税保护,决定给予多少政治捐款,还要考虑政治家如何看待社会福利和政治捐款(Grossman and Helpman,1994)。或者,一个独裁者要决定是否为了最大化他的跨期租金收入而发展经济,他还会考虑这一决定对经济和政治结果的影响,包括他执掌权力的期限(Olson,1993,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①更正式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来表述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向量a表示选择变量,向量c表示总的私人消费,α表示政治代理人可以攫取的经济剩余(或总私人消费)的比例。那么,每个代理人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为下式所示:
观念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一问题,很少被认识到。事实上,最优化问题的每一个要件——偏好、约束和选择变量——依赖于一系列隐含的观念。我将在下文依次进行讨论。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在争辩这些基本的最优化框架的合理性或效用。我的目的只是探讨观念在利益形成和利益追逐过程中的作用。




 雷达卡
雷达卡




 提升卡
提升卡 置顶卡
置顶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变色卡
变色卡 抢沙发
抢沙发 千斤顶
千斤顶 显身卡
显身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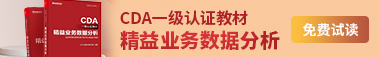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