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度”绝对是当下经济研究的核心词汇,甚至已经出现一种神话制度的趋势:凡是没想明白的内容,就先说一句“应当考虑制度问题”;凡是缺乏理论解释的现象,就归结为“制度因素”;凡是与实证检验不相符的结果,就说数据中未包含“制度变量”。似乎这样一来,无论研究成果如何,都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经济学家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研究制度的?对于制度的认识到了怎样的程度?制度研究在目前的经济学界究竟有多重要?通过分析制度经济理论获得了哪些发展?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太有趣,所以我就不揣浅陋,离题千字绕个大圈子来叙(tu)述(cao)一番。
前不久一位圈内大佬做了一次回顾制度经济学历史及其重要性的演讲,整理成文后广为流传。开篇第一句就是:“自从亚当·斯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来,其研究主体就是制度。从政治经济学一产生,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称为没有制度)……”
稍微回味一下这句话我就觉得脑子有点乱。因为如果认为制度研究很重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较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倒退,经济学是越发展越走回头路?反过来如果说经济学科还是有进步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制度研究其实是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掉的东西?
我想肯定是由于我书读得少,不知道经济学名家说的斯密时期的经济学“研究主体就是制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最熟知的斯密论及制度的内容不过就是有关中国的描述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65、87-88页)
。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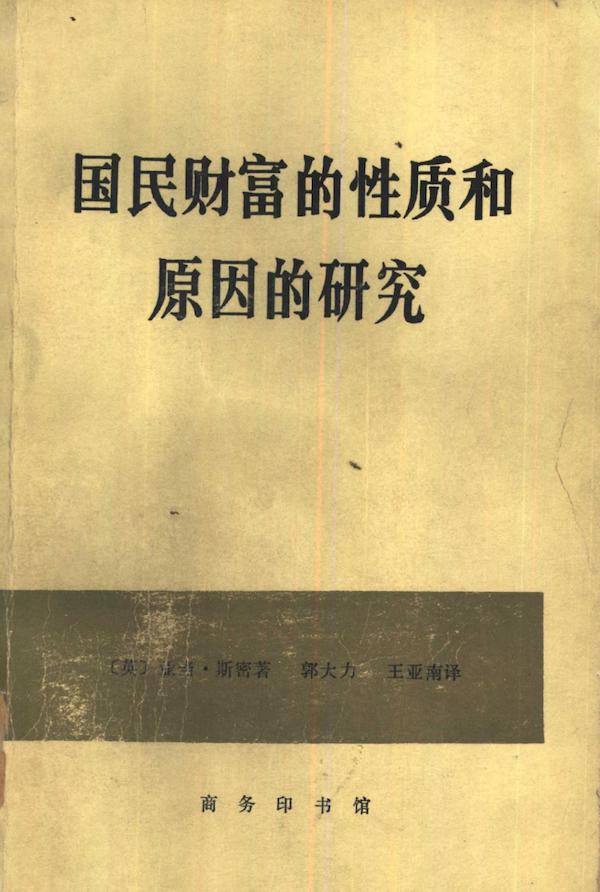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这样的论断难道就是所谓的“研究主体是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所有这些古典经济学大师谈及制度时都是这么一副“德行”:在古典经济学中,“制度”(通常还和风俗、习惯、法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般是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对于经济现象的补充性解释而存在的词汇。
倒是被誉为法国的亚当·斯密的萨伊(Jean-Baptiste Say),稍稍有点与众不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有专门的一章,“旨在影响生产的官方规定的效果”,和整本书的体系显得有些脱节,却涉及许多后世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论题,包括第一次有关“寻租”(rent-seeking)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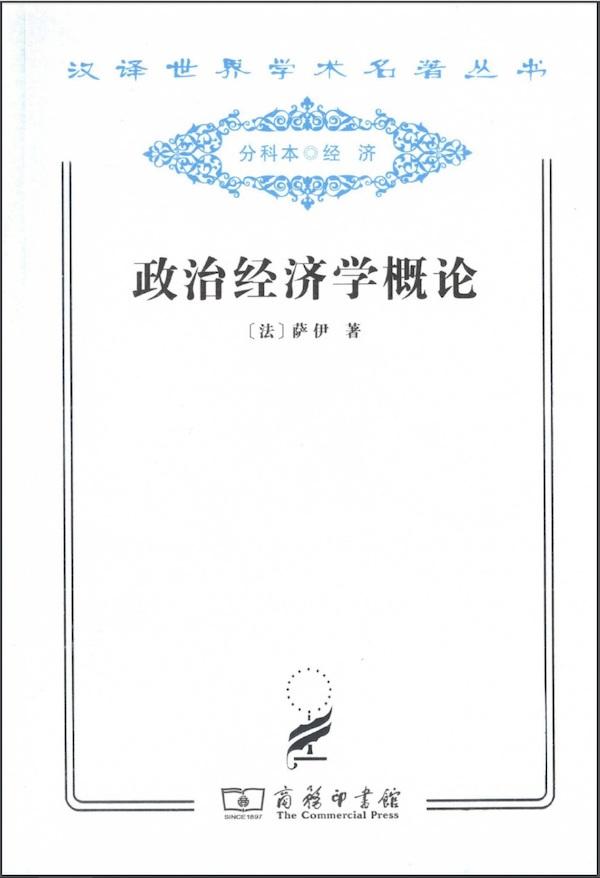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概论》
萨伊对制度现象的特别关注与法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萨伊自身的从商经历有关。然而对于英伦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也不是不关心制度问题,只是因为古典经济学体系内已经暗含了一个关键性前提假设,即经济运行规律是发生在特定社会制度情景下的。唯有如此,经济规律才能与自然规律相区分(在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的法国重农学派正是将二者混同了)。所以斯密在《国富论》中详尽探讨的经济发展机制仅仅是他的“自然自由制度”(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后来的德国学者由于搞不清楚这点,才提出了“利他”和“自利”相冲突,即所谓“斯密悖论”这么个奇怪的命题(当然,这其中还牵涉欧陆和英伦思想对经济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
将制度作为前提假设,就致使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话语内进行制度分析无比困难。这就好比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要将自己和凳子同时举起来一般。只有跳出古典经济学框架才能论述制度,斯密本人就是在《法理学讲义》等著作中详细讨论制度问题的。这一点马克思看得比谁都明白,他只需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性前提替换掉,那么原本是为资本辩护的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就摇身一变,成为了预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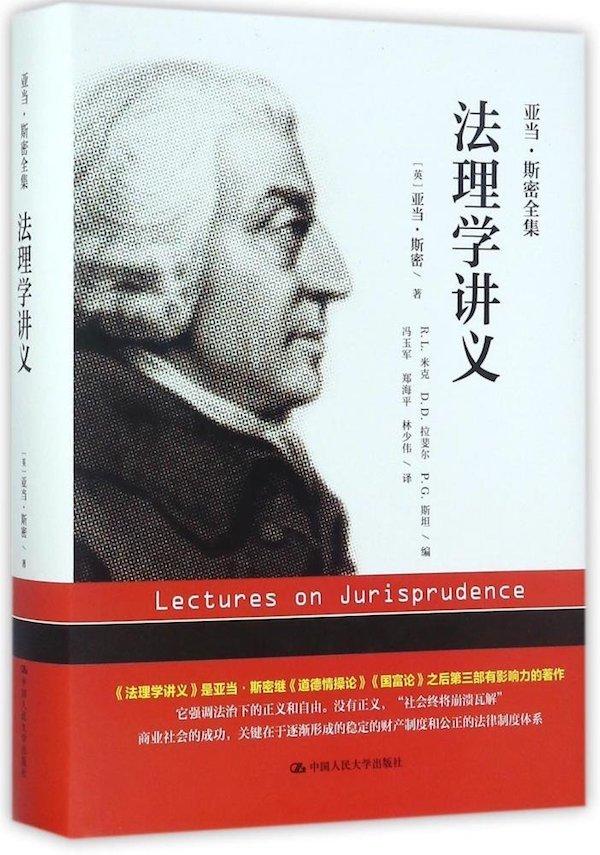
《法理学讲义》
所以说来惭愧,尽管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制度分析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朔到维柯的《新科学》(1744),但相较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这些学科来说,经济学制度分析起步很晚,而且恰恰是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出现的时候。
通常认为,第一部真正算得上“制度研究”的经济学著作,是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
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
),出版于1899年,该书副标题是“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无论是以当时还是现在的学术标准,《有闲阶级论》都算是本奇书了。全书论据没有一个出处——既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文献,甚至连修辞风格也更接近于散文而非“研究”。
因此这本书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最初评价一般,但是挡不住它在社会上的流行。因为书中那种对现实社会无情批判的精神恰好迎合了上个世纪00后青年对清教资本主义的厌恶。“有闲阶级”,连同凡勃伦这位油腻大叔(据说他个人卫生习惯极差)本身,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青年流行文化的象征:不仅有凡勃伦书籍、凡勃伦小册子,还有一群称为“凡勃伦女人”的迷妹。
如此的社会影响力自然让学者们的态度开始改观,一些学者——主要是接受德国历史学派教育的学者——开始认真“钻研”凡勃伦的著作,于是乎“制度学派”(又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作为美国原创的经济学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凡勃伦留下的最重要思想遗产之一,就是有关“制度”的定义:“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商务印书馆,1964年,139页)
《有闲阶级论》
正所谓经典永流传,一句顶万句。凡勃伦这句晦涩难懂的制度定义引发了众多学者前赴后继的无数解释。而且正因为可以不断阐发新含义,所以才能与时俱进,和不同新理论相结合,譬如时下经济学界的网红——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也能引用凡勃伦的定义为自己正名。
严格来说凡勃伦的制度定义并不费解,只是没写明出处。他有关制度的解释和十九世纪法国古典社会学的理解如出一辙,“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称为‘制度’”,该论断写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 1895)。简言之,凡勃伦传统的制度理论,突出强调了社会制度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即制度是文化。
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简单,因为“文化”太复杂了。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经济学界也没有太多合适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处理文化问题。倒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文化”也具有价值,因此可以和商品一样使用价格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被怒斥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名不见经传、忙着找份好工作的美国新移民、英国好绅士科斯(Ronald Coase),扭转了经济学的潮流。科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1937),可是没人看,要等五十多年后才能重见天日。而1959年时他又写了一篇怪文《联邦通讯委员会》,大意是说像无线电频道这类有极强外部性的物品为什么需要ZF管制呢,应该通过界定权利然后经由市场交易才会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这篇文章实际上挑战了当时已经霸占经济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权威传统,由马歇尔的学生和继任者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创建的“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最早由英国伦理学大家西季威克提出,后经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得到充分阐发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个人、企业的行为不仅对自身有影响,还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造成影响。但是个人和企业通常只会考虑自身的影响,即私人成本和收益,不考虑社会影响,即社会成本和收益,如此一来就会导致通过市场交易配置资源的模式达不到最优水平,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工厂生产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庇古提出“庇古税”方案,对造成负外部性的企业征税,使它们的私人成本增加到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同时通过转移支付对产生正外部性的企业补贴,让他们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相一致。
听上去好像很美妙。可是科斯却直言这样的经济管制是错误的,应当让市场中的权利主体自己做主,通过交易来发挥资源的最大价值。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论甚至连当时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法与经济学杂志》主编也感到有些吃不准。在要求科斯删去文中一个极易引起争议的例子遭拒后,主编仍然大度地刊发了这篇文章,但是要求科斯到芝加哥大学来和那些经济学名家对话一下。
于是乎就发生了1960年春天的那次“华山论剑”(张五常语)。参加辩论的有十人,科斯以一敌九,最终科斯的观点赢得了所有人的同意——其实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雄辩说服了所有人。辩论的结果,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作《社会成本问题》(1960)的诞生。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如今学界对这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只有十余个司法案例和法律解释组成的文献有无数种解释,连科斯后来都自嘲作品写出后解释权就不归作者了。不过从狭义上来说,科斯在这篇文献中只说了一件事:制度是重要的。
在科斯看来,没有理解导致外部性的原因就盲目去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庇古税”方案背后隐含的潜台词是“损害者赔偿损失”,可问题是这一刑事司法惯例未必就能适用于存在诸多外部性问题的民事侵权领域。因为在民事行为中,常见的情形是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损害者”,此时“两害相权取其轻”才是正确的做法。
那么为何会产生外部性呢?很简单,权利界定不明晰。仍然是工厂污染的例子,试想如果我们能明确界定企业生产的时空边界,并将其污染所至的所有空间和资源的使用权利都归属于企业(当然企业要为此付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这就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当企业老板要时刻带着防毒面具,当企业把生产所需资源全部污染,这时候不用ZF出面,企业自己就会来着手解决成本问题了,或者它就破产倒闭了。
看到这儿聪明的读者会说:可现实中这样的权利界定是无法实现的。没错,正因为真实世界中再完善的法律、再贤明的ZF、再有素质的民众也无法做到如此明晰的社会安排,所以有关产权的法律制度、有关企业生产的规章制度、有关市场交易的规则就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经济学家关注的效率问题,其实是制度依赖下的效率,制度因此而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科斯启发了一大批一流经济学者开始认真思考制度。同时八十年代博弈论兴起,博弈论专家也开始在另一个平行理论世界中研究社会制度,即博弈论制度分析。这些深受分析哲学熏陶的技术流学者为经济学家带来了解释制度的分析工具。两股思潮终于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合流,一举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思维模式。经济学从“言不及制度”转型为“言必及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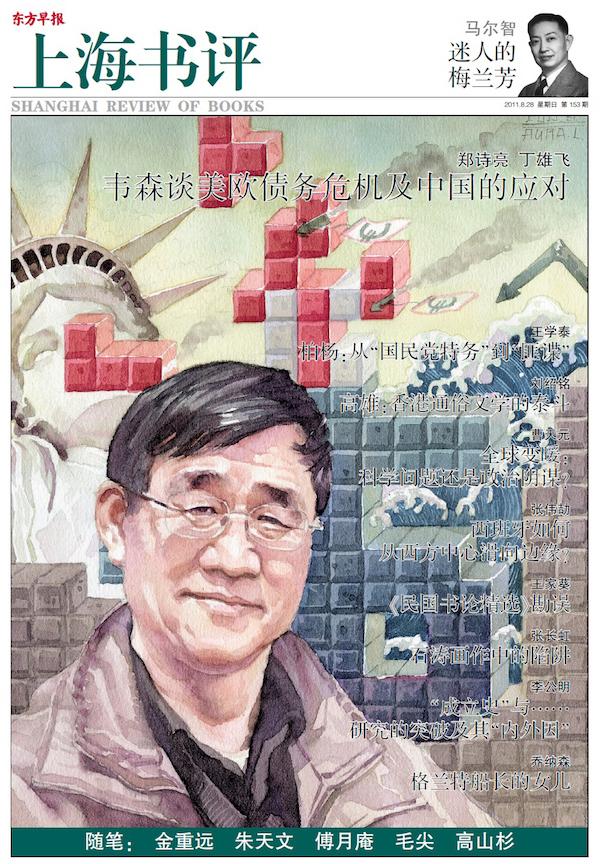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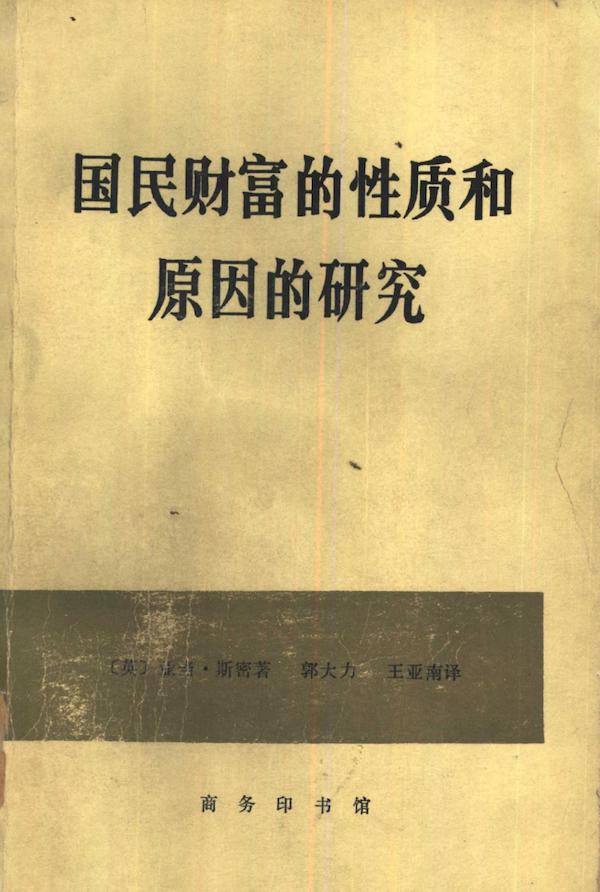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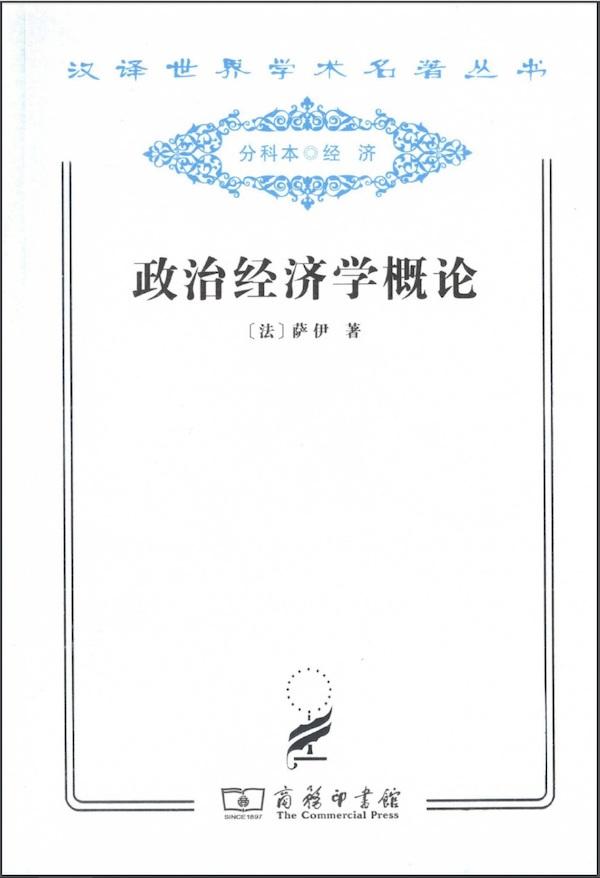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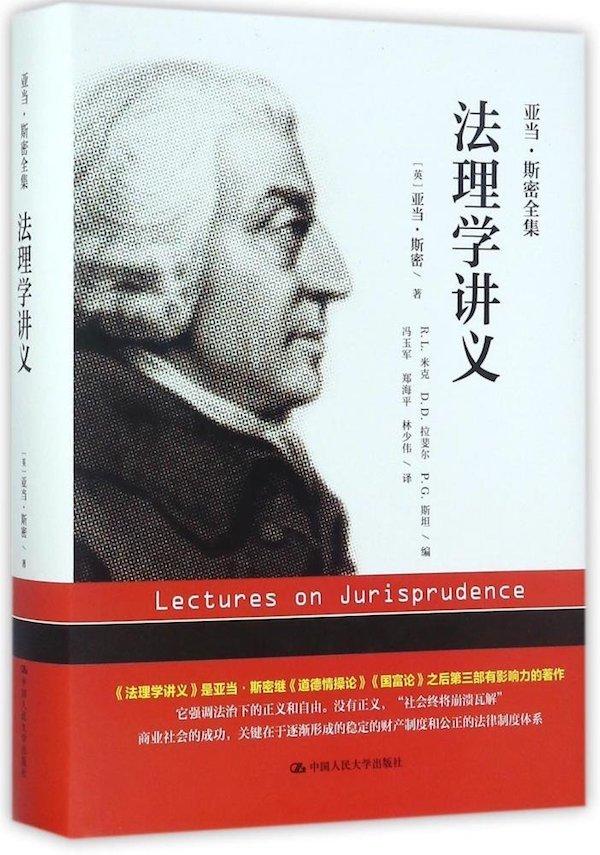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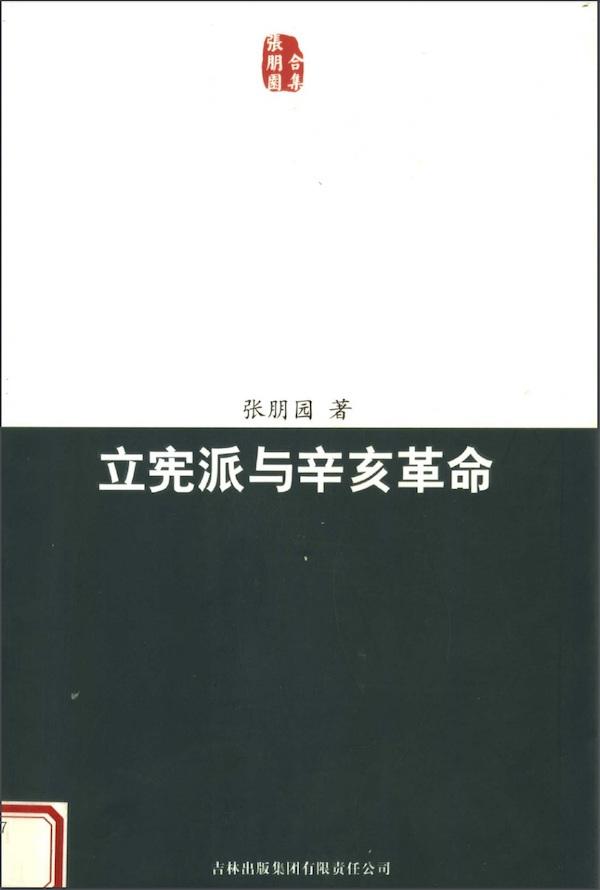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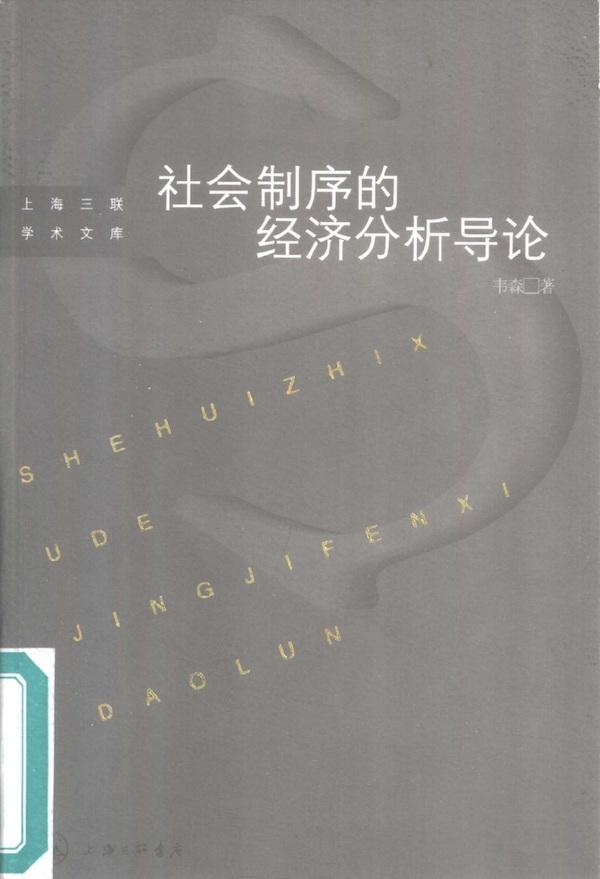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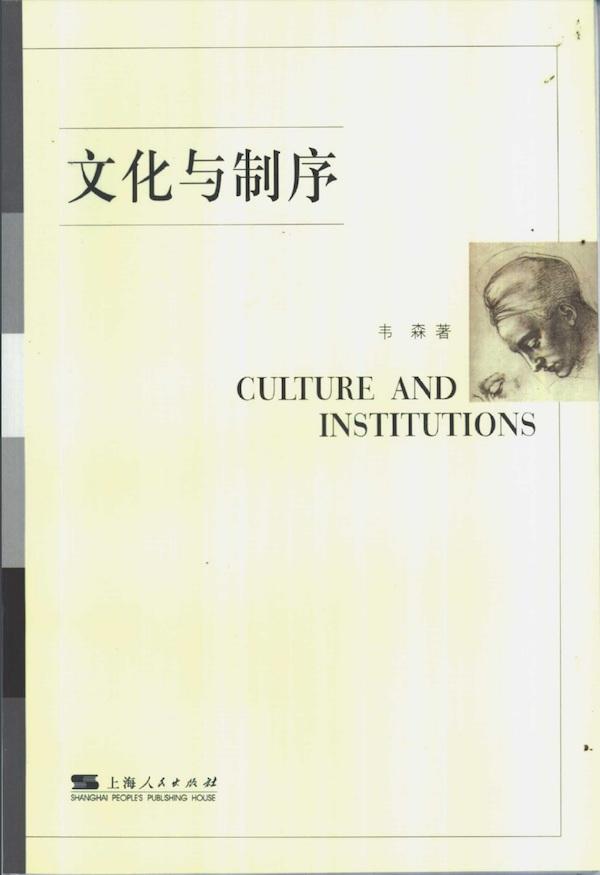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