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Shapiro and Walker(2015)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环境监管至少解释了1990至2008年间美国企业污染下降60%中的75%。然而,环境规制中的传统的监测和执法却逐渐引起了争议,通过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政策部门越来越多地提倡一个摆脱传统监管而更加关注自由和信息政策的方案。许多国家执法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例如,美国环保部(EPA)的民事执法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显著下降,许多环保机构也越来越多的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合规保障计划(CAP),最近美国国家公民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审查EPA表现时,仅仅给出了是“适当”的评价,并建议EPA加强执法管理程序(USOMB,2005)。尽管环境规制中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日渐多样化、所发挥的作用日趋凸显,但是作为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直接(行政)规制,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还依赖于环境行政机制(卢洪友等,2014),最新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严格监测和执法的监管结构依然是企业环境改善的首要驱动力(Greenstone和Hanna,2014)。
对污染违规进行监管处罚在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环保政策中发挥着支柱作用,进一步来看,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渐渐相信,有效的污染监管要求经常性的环境检查和制裁,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强调强制执行的规制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发达国家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的主导因素((Kagan et al,2003; USOMB, 2005)。虽然Khanna and Anton(2002)调查的S&P500企业表明,类似全面质量管理的第二类环境实践归功于市场因素,但是类似环境审计、内部政策等根本性的环境实践则依然源于法律和监管因素。Doonan Lanoie and Laplante(2005)发现70%的加拿大经理人将政府视为环境压力的唯一主要来源。May(2005)的研究显示,传统监管对经理人威慑力更加强于非强制性项目,最后,Delmas and Toffel(2008)通过调查493个工业污染源,发现,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显著地大于社区组织、活动团体和媒体。通常意义上的环境规制主要包括环境标准、配额使用限制、许可证等,而且还会涉及到环境监测、检查以及违规之后所进行的各类行政处罚,尤其是后者,日渐成为环境规制研究中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的研究呈现出迅速的增长态势,归结起来,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一是环境规制不再仅仅作为一个整体被研究,环境规制中所涉及到的监测、检查以及违规处罚等逐步进入研究视野,尤其关注环境执法所产生的威慑遵从效应。 二是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探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再分配效应。逐渐从单纯的减排或者经济成本,扩展到社会领域,分析的主体日益多样化,包括企业、工人、辖区居民、社会整体福利,未被监管者或者处罚者等。三是环境规制如何与其他环境政策协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新焦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单纯依赖某一项环境规制政策已经独木难支,强化不同环境政策之间的协同和协调,对于提高整体的环境规制效率,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扭曲显得尤为重要。四是有关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净效益的评估更为全面客观,表现在,逐渐考虑了环境规制所产生的健康收益、就业再分配成本、劳动生产率改进收益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和评估环境规制福利效应大有益处。
环境监管的“减排”效应
从理论上讲,环境规制理论是建立在由Becker(1968)和Stigler(1970)发展的法经济学和公共执行理论文献上,并由Russell、Harrington 和Vaughan(1986)将该理论运用到环境领域,Polinsky和Shacell(2000)做了详细评述。环境境规制的本质是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采取多种行政手段(如限排、定额、许可、警告、罚款、限产、关停等)提高企业环境违规的成本,只有当企业环境规制所产生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环境违规的所得到的边际收益时,才会达到均衡,即停止污染增长。边际成本时取决于公共部门(主要环境行政机构)的执法严厉程度,而边际收益则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前提是处于竞争市场中),而现实市场均衡必然会受到包括环境规制在内各种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本身的执行。在此框架下,那些不完全控制排放额的企业可以从更低的污染减排努力中获得经济收益,企业会权衡更低减排努力的收益和被发现违规时所产生监管处罚的潜在成本,这一权衡意味着,企业有关污染减排努力的决策是这些因素的函数:减排努力条件既定下感知违规的概率;如果违规,感知被检查的概率;如果被检查,感知被处罚的概率;如果被处罚,有关处罚程度或幅度的认知度。
实证方面,评估政策干预对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从一般意义上将,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一是制造业贸易的大幅增长((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 Pierce and Schott,2012; Fowlie, Reguant, and Ryan,2015),这是因为类似钢铁、水泥等污染行业转移到国外,使得国内总污染排放在下降;二是规制能力的提升,规制机构要求企业逐步安装升级日益严格的污染治理设备和技术,如在美国,一些研究将其直接归功于清洁空气方案及其他环保法规实施所带来的空气质量变化((Henderson, 1996; Chay and Greenstone, 2005; Correia et al, 2013));三是偏好的变化,社会公众越来越多地选择消费清洁用品而非重污染行业生产的产品(Levinson and O'Brien, 2013);四是效率的提升,如果制造商使用更少的污染投入而生产了相同的产出,那么每年生产率增长是可以改善空气质量的,企业层面的单位产出排污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负向关系,全要素生产率在上升,而单位产出污染排放在下降(Bloom et al, 2010; Holladay, 2011;Martin, 2011)。在美国的制造业部门,1990-2008年大多数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却下降了60%;从1990-2000年,美国制造业真实产出增长了三分之一,而主要污染物来源的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平均下降了35%;2000年之后,真实产出增长下降,而制造业排污量在1990年基础上又另外下降在25%。Shapiro and Walker(2015)发展了一个可以用国际贸易、环境监管、生产率和消费偏好用来解释污染排放的量化模型,作者使用企业层面生产和排污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了估计,然后将这些估计与历史数据相结合,进而提供了一个解释可观察污染变化原因的可分解模型,发现,污染排放下降主要由于用一个狭义产品来度量单位产出污染,而非使用了总的制造业产出总量或不同类型的产品来度量;用于合理化企业生产和减排行为的隐含排污税在1990至2008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环境监管能够解释可观察污染污染排放下降中的75%。
环境检查和执法的威慑遵从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主要取决于环境检查和执法所产生的威慑以及由此所带的遵从。受到环境法律(如清洁空气法案CAA、清洁水法案CWA、以及环境规划和社区法案EPCRA)监管的许多工厂被要求定期提交自我监测报告,包括有关遵从和排放的主要信息及其来源。对于小工厂和不太突出的监管,遵从和排放数据往往只在被监管检查时才被观察到。监测活动的范围从持续几小时的快速目视检查,到持续一个月以上更严厉的评估。许多检查包括排放检查以及减排设备安装、运行和维护检查等。其他监管机构的监测活动可能包括自我评估、记录和程序、广泛的访谈以及污染排放的采样调查。当前的EPA合规监测策略建议CAA的完整合规性评估至少每两年一次,并将排放超过门槛值80%及以上的归类为主要排污源,要求每五年至少一次完整的合规性评估(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 2001a)。
针对违规的执法行为包括电话和信件警告、罚款和刑事检控,非正式的执法行动通常是由地方环境行政机构执行。虽然少数州的环境机构有权发出现场行政处罚,但是大部分罚款和其他制裁是需要通过国家或地区EPA行政法院的行政法规来实行。文献几乎一致认为,严厉的环境监管具有较大的威慑效应,例如Magat and Viscusi(1990)发现平均检查后,被检查工厂的常规水污染排放会相继减少20%;Gray and Shadbegian(2005)发现,平均处罚会使得违规企业数量相对下降10%;Shimshack and Ward(2005)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大量可观察到的环境绩效改善应该归功于环境监管和执法行为所引致的传统经济激励和约束,而非企业社会责任、理他主义、或非强制性压力等。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增加环境规制和执法方面的少量投资就可以显著的提高环境质量。如果目前的标准并不过分严格,执法成本适中,那么由执法行为所引起的企业行为变化就可能转化为较大的社会福利收益。
环境规制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在正式监管中,政府被看作是社会公众的代理人来对工业污染进行控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传统分析就会认为污染是没有成本和基本上不受约束的。但是,一些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证据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些正式监管减弱或消逝的发展中国家中,许多社区已经取得了与当地企业就污染减排进行谈判博弈的能力。这可以进一步称之为非正式监管: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做主,随着污染损害上升,社区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为企业提供相应的环境资源,伴随着预期处罚增加,工厂会想方设法降低其对环境资源的需求。
信息和交易成本是影响均衡的重要决定因素:社区在进行博弈时面临着企业层面排放和风险信息稀缺的难题,没有从法规层面确定追索权,他们必须依靠工人和管理人员、负面宣传、暴力威胁、诉诸民法或者通过政治家、本地行政官员和宗教领袖提供形成的社会压力。这一过程区别于国家和地区正式监管, Pargal and Wheeler(1996)发现当正式监管较弱或匮乏是,社区往往会在非正式监管的过程中使用其他途径来引致地区企业的减排,污染均衡结果反映了地是社区和企业的相对博弈和谈判权力。作者使用印尼1989-1990年企业初始水污染排放数据验证了非正式监管的假设,印尼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会对包括非环境政策在内的其他变量做出高度响应。同时作者还发现,老的非生产性企业是新企业和生产性企业水污染排放强度的2.4倍,公共部门企业的污染强度是私人部门的5.4倍,落后和监督程度不高地区的企业是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地区的15.4倍。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的建立自愿型自我报告程序作为调查工具并鼓励受监管的企业遵从承若, Delmas & Toffel(2011)研究了自愿型自我报告能否有效有效可靠的表明自我管理努力(提供执法效率机会)。Langpap and Shimshack (2010)探讨了私人而非公共执法的影响,私人执法行动显著的提高了环境遵从,但是当把公共执法排除而单纯考察私人威慑效果,是非常脆弱的。
(未完待续) 作者 马倩林、祁毓,文章来源:香樟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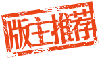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