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这一行业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传统的铜匠业的操作方式之后,我所从事的行业就迅速地衰微了,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调动工作时难以继续做铜匠的工作。但是因为铜匠这一行业乃是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常能在诸如管道安装、钢板和工业设备等行业中找到工作。我在铁道修配厂、钢板厂,特别是两家把钢板和结构钢加工成为基础钢铁工业用的设备(包括鼓风炉)的工厂里,做这一类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这种关于技艺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作出结论说,我对古老的劳动方式的陈腐条件还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但我力图不让我的任何结论根据这样一种浪漫精神来作出,同时从总的说来,我不认为这个批评是有理由的。的确,我过去乐于,现在还乐于以一个手艺工人的身份进行工作,但是因为我是在机械技术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识到以科学为根据的技术变革在不屈不挠地进展着;而且,在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里,在我所参加过的工匠们关于“新”与“旧”的许多次辩论中,我总是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劳动过程之从以传统为根据转变到以科学为根据,这对人类的进步和使人类免于饥饿和其他穷困来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那些年中,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所敌视的并不是科学和技术本身,而只是把科学和技术用作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并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种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我像所有的手艺工人,甚至最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手艺工人一样,老是忿恨这种事;当我重新阅读本书时,我感到其中不仅有一种社会的义愤感(那是我故意写出的),而且也许还有个人的受侮辱的感觉。如果确是如此,那我说,这并不是我故意写出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害处。然而,我重复说一句,我希望没有人从此得出结论说,我的观点是由于缅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关于工作的一些观点都是由于怀念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里,对工人来说,由于自觉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劳动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技艺上的满足,将与科学上的奇迹和工程上的独创性结合起来;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从这种结合中得到好处。
在后来的几年中,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某些最典型的办公室劳动过程开始经受急剧变化的时刻,我能得到关于它们的第一手经验。干了几年社会主义报刊工作之后,我就在书籍出版方面当了一个编辑。后来又在两家出版社当了十多年的业务管理人员。在这里,我能够了解到、事实上也能够设计出某些涉及现代销售、分配、会计和书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过程。而这个经验又包括从传统的办公室体系到计算机化的办公室体系的转变。我并不自认为这一背景同许多长期在大机关里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样广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当详细而具体地了解现代办公室据以组织劳动过程的那些原则。
读者们将在适当的章节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书中利用这一经验。我还得益于许多朋友、熟人和在公开集会上或旅行时所遇到的陌生人所进行的关于他们的工作的谈话(现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读到本书的话,可能会了解为什么我那时竟那样直率无礼地爱打听这类事情)。但是,虽然这种职业的和谈话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还必须强调说,本书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个人经验或个人回忆而提出的;我纳入本书的那些实际材料,几乎没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处来,使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这是任何科学作品都应作到的。
在整个研究和编著的过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讨论了那时正在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这里为他们的关心和耐心向他们道谢。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关心的人们读过,我得感谢他们的一切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使我对于有时是很复杂的题材表达得较清晰些,并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达上的错误。我要特别感谢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他们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会忽略的线索,并建议我阅读一些我可能会漏掉的材料;但我还要加上一句话,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主要好处,也是我最深切感到的好处,乃是他们为我树立了作为企图掌握现代社会真实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我对那些其著作具有特别价值的作者的谢忱,俱见于本书正文以及脚注和出处注释中。本书是在马克思的精神影响下写成的,但是,读者将会看到,马克思以后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书,都没有在本书的有关劳动过程的那些章节中发生直接的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设法加以说明。
※ ※ ※



 [em29]
[em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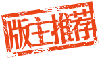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