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资本论》揭示的资本总公式 G-W-G' 基础上,当代虚拟资本的演化已突破传统理论框架。本文以“新概念资本论”视角,重新审视虚拟资本与生产资料转化的关系,提出“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分层理论,阐释金融化时代资本增殖的双重路径及其制度调控逻辑。
一、经典框架的当代挑战:虚拟资本的脱嵌与异化
(一)生产资料转化的本源逻辑解构
新概念资本理论认为,货币(G)转化为生产资料(W)是资本增值的物质基础。在19世纪产业资本主导时期,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确以筹集生产资金为核心功能——如1870年代美国铁路债券融资推动铁轨与机车的大规模生产。这种“G→G'→W”的转化链条,使虚拟资本成为连接货币与生产资料的中介。
(二)金融自我循环的现实背离
当代金融市场已呈现显著异化:2024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达 400万亿美元,其中仅15%流向实体生产领域(IMF数据)。以加密货币为例,比特币市值曾突破 3万亿美元,但其交易完全脱离生产资料转化,形成“G→G'”的纯符号增殖。这种脱嵌现象迫使理论框架必须回应:虚拟资本是否已形成独立于生产的运作逻辑?
二、二元资本结构:虚拟资本的分层理论建构
(一)一级虚拟资本:生产性转化的守护者
定义:直接服务于生产资料购置、技术研发等实体活动的金融工具,遵循 G→G'→W…P…G'' 的增殖路径。
一级虚拟资本的典型形态是产业投资基金。例如注资新能源车企建设电池工厂的产业投资基金;政府专项债用于高铁轨道等基础设施生产资料投入。
一级虚拟资本的核心特征是价值增值必须以生产资料转化为前提,与工人劳动(增加就业)创造的剩余价值形成直接关联。
(二)二级虚拟资本:符号化增殖的狂欢
定义:二级虚拟资本是以一级资本为标的进行衍生交易的金融工具,本质是 G→G' 的货币游戏,与生产过程完全割裂。
其典型形态是投机资金。例如量化基金通过ETF套利获取价差收益;投机者炒作粮食期货推高农产品价格,与实际种植规模无关。
二级虚拟资本风险极大,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中,CDO(担保债务凭证)规模达 6.2万亿美元,其层层嵌套的交易链彻底脱离房屋生产现实,最终引发系统性崩溃。
三、剥削机制的升级:从剩余价值分割到符号化掠夺
(一)传统剥削路径的式微与转型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产业资本雇佣工人生产商品(W)→ 金融资本以利息形式分割剩余价值(如19世纪英国纺织厂债券的利息来源)。
金融资本主义时期:
二级虚拟资本通过资产价格通胀 直接掠夺社会财富。美联储2020年推出的无限QE政策,使美股前10%富豪持有市值增长70%,而底层50%家庭实际财富缩水12%(美联储数据)印证了“符号化掠夺”的高效性。
(二)数字时代的新型异化
NFT、元宇宙资产等新型虚拟资本创造“数字稀缺性”幻觉,宣称“用户创造价值”,实则掩盖剥削本质:
案例:某NFT项目以“虚拟土地”为标的,单价炒至 600万美元,但背后无任何实体资产或生产资料支撑,最终90%投资者面临归零风险。这种“共识定价”机制将劳动异化延伸至数字领域,劳动者(如NFT创作者)仅获得微薄收益,而投机者攫取主要增值。
四、生产资料转化的制度调控路径
(一)一级资本的强化机制
1.定向金融工具创新:
设立“硬科技转化基金”,要求风投机构将不低于40%资金投向芯片光刻机、新能源材料等生产资料领域;
2.税收杠杆引导:
对投入实体生产的一级资本减免资本利得税(如中国对高新技术企业债券的税收优惠)。
(二)二级资本的约束框架
1.交易成本调控:
征收0.5%金融交易税(托宾税),抑制高频投机交易——据测算,该税率可使全球衍生品投机规模缩减 30%(UNCTAD研究);
2.功能隔离制度:
推行“金融业务牌照分类”,禁止商业银行将存款资金投入二级资本交易(类似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五、结论:资本总公式的当代重释
虚拟资本的运作本质已演化为“双重逻辑并存”:
生产性维度:一级资本延续“货币→生产资料”的转化传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撑;
寄生性维度:二级资本构建“货币→更多货币”的符号游戏,形成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掠夺。
新概念资本论的核心启示在于:若要回归资本服务生产的本质,需通过制度设计强化一级资本转化效率,同时遏制二级资本的无序扩张。这要求重构金融监管逻辑——从“放任创新”转向“功能导向”,使虚拟资本真正成为生产资料转化的“催化剂”而非“腐蚀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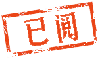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