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陈嘉映先生在《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中国问题·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中讲到:西方从占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
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 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超,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 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 作为人家的理论的一个例证。
总的说来,西方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跟政权的联系相对松散,更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不像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是作为帝国体制中一个稳定的阶层存在的,与政权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这两千年的政治史,反过来说,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也就没有中国土大夫阶层这种特殊的群体。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大夫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 他们的研究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士文化中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
我们讲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老百姓不问制度只盼清官,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士大夫之所以要服从于皇帝,是因为需要皇帝的权力,皇帝赋予他权力才能来保证民本的实现。所以他们劝谏皇帝,上疏、进谏,有时候是木要命的,如海瑞抬着棺材去给嘉靖皇帝上疏。 不过,中国的官不能完全理解成为韦伯意义上的纯粹工具理性的官惊,他是要传“道”的,这在士大夫阶层中表现的往往非常强烈而不论成败与否,这大概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一个大致由来。中国的民俗文化如此强悍的延续至今,不能不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民主的意识相关的。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的思想是因士大夫阶层的存在而存在的。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中更多的是士大夫阶层通过落实民本思想来保障社会的安定和富足,与这种自上而下的“给予”截然不同,自古希腊城邦文化以来,西方更多的是通过每一个公民自己以及公民社会进行权利上的斗争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虽然今天的中国跟传统上的中国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但这一特点仍然随处可见,在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上仍然相当明显。
总之,当政治扭曲了人们的智性思维,这个社会制度就有问题了。
下面附文,或许讲出一些西方学者的道理。
郑永年:不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创新就是空谈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很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再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画,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和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象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有再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这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而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 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摘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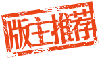
 扫码
扫码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
知识产权保护声明
免责及隐私声明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
知识产权保护声明
免责及隐私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