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学院研讨会参加论文》、《中国计量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但是没收到该杂志】
从计量、测量角度看价值是什么
提要:原本以为《资本论》中是从计量和测量的角度引申出价值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利用这对概念从汉语角度解释价值是什么,以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应用,结果发现《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这样工具书籍中的解释,也是计量与测量不分,所以文中对这三个概念一起谈谈个人的理解和看法,从而摆脱《资本论》中最大的逻辑困境,即价值有什么用?资本家为何剥削它?
对此,文中认为价值就是财富的量,劳动时间就是测量财富多少的一种尺子。但是这种尺子普适性很小,它不能测量天然商品价格的大小,比如不能测量原始森林、原始土地、石油、沙漠、海鱼等商品的价格;不能解释工资的高低差别,比如为什么工资水平越来越高?为什么同样的劳动支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工资不一样?等等。
关键词:计量、测量、价值、价格、财富分配、价值转型
什么是数,什么是量,什么是数量,这是价值理论背后的根。只有理顺这个根,我们才能真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做出继承和发展。
12345就是数,数与计量单位组合在一起,就是数量。比如9与米结合就是9米,9与斤结合就是9斤,其中9米和9斤就是数量,米和斤是数量的计量单位。计量单位就是事物的特征符号,用来标明数量的类别是什么的一种概念——量纲。比如9个人和9头牛这两个数量中,“个人”表示是人类,“头牛”表示是牛类。显然,人类又分白人、黑人和黄人,牛类又分黄牛、白牛和花牛。对事物的分类和计数的大原则就是如此。记忆中原来的《新华字典》后面附有七种国际基本单位制表,现在只有《现代汉语词典》后面附有这张表。
《资本论》中认为价值的计量单位就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所以就有商品价值是9小时、9天这样的数量。显然这种数量——即价值的多少,与时间的多少混为一体了。发展马克思价值理论首先要纠正这种量纲混乱。
一、从计数规则上看劳动价值论中的固有问题
使用价值是以人为本而定义的一个概念,是指商品中对人类有用的特性。比如大便对人类来说是废物,没有使用价值,但是对于狗类来说它是一顿美食,有使用价值。所以使用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它有用还是无用要因使用它的主体而定论。
价值是描述使用价值有多少的一种概念,是人们杜撰的一种概念,客观世界没有价值这种东西,所以不可化验。这种杜撰与杜撰数字12345一样,是意识范畴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说价值不可化验,就是指这种意境,只是马克思的相关描述晦涩难懂。
从商品角度看,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固有的特性,是客观的;价值是对使用价值有多少的计数,是主观的。另一方面,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商品的各种不同用途的一种抽象描述,抽象后统一叫作使用价值。比如大米既有充饥的性能、也有酿酒性能、也有做浆糊的性能等等,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统一叫作使用价值,在效用价值理论中统一叫作效用。这就是说使用价值可以直接计数。马克思说使用价值不可计数,是将某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混为一体了,即将事物在不同阶层的性能混为一体了。这好比人类本身是有千差万别,先是有白人、黑人和黄人之别,后有男人和女人之别,再有婴儿、年轻人和老人之别,但是都被我们抽象为“人”,从而可以统一计数。于是不管身高、体重、性别等等的差异,一个婴儿的计数是1人,一个大人的计数也是1人;一个女人的计数是1人,一个男人的计数也是1人。马克思的这种逻辑问题,如同说大人和小人体重不一样,男人与女人性别不一样,所以他(她)们间不能统一计数。
能不能统一计数与抽象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比如抽象到“生命”这个程度,则一只猫与一条狗之间也可以统一计数,等于2个生命。依此不难发现,我们可以直接从财富量的角度对各种商品直接计数,用货币作为计数尺度。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从财富量的角度得出的一个概念。
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千差万别,不可计数,要从价值角度来计数,这可能是在于计量和测量知识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还不普及,所以出现误判。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则明显表明马克思数学功底不足,这进一步导致马克思的误判变成不可理解。
从个人研究看,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是《资本论》中一个纯粹多余的一个概念。马克思所谓抽象法实际是平均法而已,但连平均法也用错了。马克思是将劳动力平均掉后才认为价值的多少要用时间来测量,并用日、小时作为计量单位。这是很明显的量纲挪用,直接导致劳动中的主导因素——劳动力居然与价值的多少无关。所以,《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是劳动时间价值理论,只能算半个劳动价值论,另半个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力价值论,被他平均掉了,不曾研究。真正的劳动价值论,一定是劳动力价值论+劳动时间价值论。
平均法是我们解析问题时的一种常用手法,但是有个要求,不能平均掉,让其消失,而是必须用平均常数k其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该用kt来表达,而非他说的用劳动时间t来表达。
如果不使用平均法,对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一起解析,利用微积分进行运算,我们很快就能得出价值(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以劳动时间这个结论,即q=kt。这才是劳动价值的求算公式。
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个数学问题,于是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打一个补丁。其实,倍加关系不外是复杂劳动中支出的劳动力t大一些。比如正教授的工资比副教授高,在于正教授支出的劳动力t大一些,二者的工资差别可以用q=kt直接求算出来,不需要倍加关系这个补丁。
二、对测量知识的介绍
这里先介绍一下测量知识,以便我们知道《资本论》中的关键失误是什么,以及《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要修正什么。
测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测量,一种是间接测量。直接测量是从事物中选择一个标准个体做尺子,去测量其它个体的某种量有多少;间接测量是指用别的事物做尺子来测量本事物有多少。比如用手指背的温度测量婴儿的体温有多少就是直接测量,即用体温测量体温。但是用水银温度计测量体温有多少就是间接测量,是用长度(汞柱高)测量体温。类似,用米尺测量路程有多少为直接测量,用地图导航测量路程有多少就是间接测量。
了解这些计量和测量的基本知识后,我们再看《资本论》,很显然其中对计量和测量的相关知识把握不准,出现不该出现的混乱。对比1954年和1975年两个版本的《资本论》,我们就能感知到实际中的问题有多严重。这里引用1975年版《资本论》中的一段话。原文如下: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那末,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 是用它所包含的 “形成价值的实体” 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 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对这段话中的关键词词加注着重号以突出显示,以便于我们讨论和分析。1975年版《资本论》中“计量”一词在1954年版《资本论》中都是“测量”。显然,1975年版《资本论》中的“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是一句病语,因为小时、日等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何来“尺度”一说?在1954年版《资本论》中这段话是“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部分,例如小时、日等等去测量”,这要通顺许多,但是仍然是病语,只是病症轻了许多。
1975年版《资本论》中,计量一词出现三次;1954年版《资本论》中,测量一词出现三次。这足见计量和测量这两个概念对我们理解价值是什么有多重要。但是很显然,我国不曾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考究价值应该是什么。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巨大缺憾,所以我们得从计量和测量的角度讨论价值究竟是什么。
两个版本的《资本论》中的共同问题是,都将时间的计量单位当做测量时间多少的尺子。这是很明显的错误,让钟表这种真正测量时间多少的尺子——计时器,何颜以堪?
这种错误的核心之处是,劳动力为何对价值的多少没有贡献?要知道劳动力才是劳动中的主导因素,劳动时间只是积累因素而已。所谓劳动不过是劳动力在时间上的延续,仅此而已。
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的运动都受时间的严格制约,时间是所有事物共同的特征量,而非仅仅是劳动的特征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时间角度区分那些人类活动是劳动,那些人类活动不是劳动。我们只能从劳动力t这个角度来鉴定那些人类活动是劳动,那些人类活动不是劳动。因此有这样的质疑:当劳动力对价值没有贡献时,还能叫作劳动价值论吗?叫劳动时间价值论是不是更贴切一些?
例如我国农村在大集体时代,通常情况下男人劳动一天计10分,女人劳动一天计7分。这不外是男人力气比女人大些。城市也有类似现象,比如码头工人的工资就比清洁工人的工资高。显然这里不涉及马克思讲的倍加关系,必须用q=ft才能讲清楚。
毫无疑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经不起数学检测,因为没有马克思使用的这种平均算法。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也心知肚明,所以就打了一个补丁,即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
三、从数与数量的关系上看劳动价值论中的固有问题
《资本论》中对价值的计数是依照反比律进行的,这种缺陷在以谷书堂、苏星、钱伯海和程恩富、王振中、蔡继明等为代表的两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下,已经纠正为正比律。但是问题还没有真的被解决,所以这里还要从数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自然界本身没有数这个东西,数只是人类为了计事而杜撰的一种东西。早在远古时代,先祖们在生产活动中注意到这群羊与那群羊在规模上有差异,有大与小的区别。表述大与小的概念叫规模量,即所谓的规模大、规模小。但是随着历史进一步推移,先祖们发现“一群人”、“一圈羊”这样的规模量不够用,不能描述大多少和小多少,于是发明一些计数法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堆石记数、结绳记数、刻痕记数等等,以将大、小、多、少这种规模量数量化。这种数量化就是当今自然科学皇冠——数学的始祖。
个人认为刻痕记数是个转折点,我国古代的筹算数字明显保留刻痕数字的痕迹。我国的算盘就是依照刻痕计数发明出来的。它可能就是今天的阿拉伯数字0123456789的最初萌芽。与计数相配套的就是进制。早期的进制五花八门,既有六十进制,也有二十进制、十六进制等等,现在统一为十进制,即满十进一。阿拉伯数字0123456789就是按照十进制发明出来的。数字0123456789与量纲(计量单位)组合在一起就叫数量,比如3个人、4头牛、5斤谷等等数量。
价格和价值都是经济学量,属于数量范畴。价格的计量单位是明确的,即"元/件”这种形式,那么价值的计量单位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价值的计量单位是“小时、日”等,这既是量纲挪用,也是学术越权。不仅如此,这里还隐藏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即劳动中的主导因素——劳动力f为何对价值没有贡献?
四、计量与测量的定义
《资本论》中是从计量和测量这两个概念引申出价值这个概念的,所以搞清楚计量和测量的内涵,对我们理解并定义价值是什么,十分重要和必要。
个人对计量和测量有一点认知,与我国正规教育没有关系,而是得益于一系列科普读物和《科学哲学导论》一书,二者都有只言片语提及经济学,大意是说经济学领域的计数不符合相关规范,不提也罢。
原本以为只是《资本论》中对计量和测量的知识把握不准,于是就从《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网络三个途径查询计量和测量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但是这三个途径的解释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计量与测量解释的原文如下: 计量是指把暂时未知的量与一个已知的量做比较,如用尺量布,用体温计量体温。 测量是指用仪器确定空间、时间、温度、速度、功能的有关数值。
在这里计量与测量没有什么区别?个人认为没有区别,是同一种意思,都是指测量的意思。
为此又去买一本《新华字典》,里面说“计”是指仪器,比如时计、温度计、血压计;说“量”是用器物计算东西的多少或长短;说“测量”是指利用仪器来度量。但是没有查到计量这个词汇。
那么何为计量?何为测量?我国没有这种知识教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只是一种历史知识而已,不仅是学生们不知道何为度量衡,教授们也并非一定都知道何为度量衡。
(一)何为计量?
计量就是指对计数单位及其进制的规定。比如规定某地方的一个标准直线距离为1公里,则这1公里就是测量其它地方距离的尺子。这样,如果AB两点间的直线距离用这把尺子去测量,有1.5尺这么长,则AB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将记为1.5公里。毫无疑问计量属于法律强制,即规定。
秦始皇制订的重量进制是十六进制,即十六两等于一斤。半斤八两就是借用十六进制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成语。这个进制沿用了二千多年。我国于1959年由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于是我国计量规则与国际计量组织接轨,比如重量的十六进制改成十进制,即十两等于一斤,也即满十进一。此后,全国各个方面得计数规则逐渐改成十进制。
请注意《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中的“计量制度”一词,它明确说明计量是法律层面的事情,是法律强制规定。这也表明《资本论》中规定价值的计量单位是小时、日等,是越权行为。作为学术,在法律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之前,只能用“价值有10单位”这样的语句来表达。我国少数学者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多数学者还是沿用马克思的表达方式,说“价值有10小时”。
这种规定,现在由国际计量组织完成,主要采用十进制。比如测量物体质量多少的标准砝码叫国际千克原器,存放在法国,并定义这个砝码本身的质量为1千克。国际千克原器的作用是,如果某地方使用的砝码、秤砣随着时间推移磨损了,不精确,就到国际计量组织去校对。
目前,国际计量组织规定的基本量有七种:长度、质量、时间、电流、温度、物质量、发光强度,它们对应的基本计量单位是:米(m)、千克(kg)、秒(s)、安培(A)、开尔文(K)、物质量(mol)、发光强度(cd)。其中,安培、开尔文和坎德拉是三位物理学家的名字,以纪念他们的杰出贡献。
(二)何为测量?
测量就是依照计量局给定计数规则从事实际勘测的行为,即测量是对计量的实施。它包含测量原理和测量操作两部分。
学生从初中开始到博士毕业,其中理工科类学生要不断学习化学原理、力学原理、电学原理、医学原理等等知识,所有这些知识在本文都属于测量原理。牛顿、爱恩斯坦和孟德尔等等科学家所创造的这规律那规律,这定律那定律,在此统称为测量原理。实际的测量行为是依照这些原理进行的,坚持的是正比原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三角形面积等于二分之一底乘高”以表明他要讲的共通物是什么,这是不恰当的比喻,因为“三角形面积等于二分之一底乘高”只是面积的一种测量原理,而非共通物。我们不能因此责怪马克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国现在的专业机构、专业词典及专业学者,都没搞清白计量与测量的区别,都不能清晰定义它们。
(三)何为价值?
马克思是从尺度开始逐步引申出价值这个概念的,原文是:为此等有用物的量发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的多重多样,一部分是由于待测量的对象有多重多样,一部分是由于习惯”。
请注意其中的“量、尺度、测量”这三个关键词。显然自从价值这个概念诞生后,其“尺子”的意境就在《资本论》中消失了,不见了。从整个《资本论》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测量价值多少的尺子,还是价值的本身,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直接导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很难理解,很难指导实际,从而导致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占据统治地位,成为显学。
我国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学术界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即天然物品的价值和价格问题,比如原始森林、河沙、煤炭、石油、野兔等的价值和价格,该如何核算?我们只有定义价值是财富的量才能解答这个问题。此时,劳动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每件商品分得社会财富的尺度,而非它本身就是价值。比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的人均工资,北上广深就比武汉长沙高,这不外是人均创造的财富量在北上广深多些。总之,群体创造的价值总量(财富总量)多,则其人均工资就高。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正比关系呢?不外乎是工资要随产出的增加而不断增加,不然多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式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多数国家都有最低工资法案,并没有听信西方经济学的自由思想,去当守夜人。毫无疑问,最低工资是随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而不断提高的。
所以劳动时间只是人们分得工资多少的一种尺子,但是《资本论》中将这种尺子当做价值本身,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解释实际价格现象的根本原因。比如同样扫马路,为何北上广深的工资比武汉长沙高?
(四)何为价值分配?
价值分配就是价值转型,它是描述财富分配一个学术概念,以阐述相应的学术原理和规则。
个人的研究表明价值不能直接决定价格,而是要分配,只有分配后各个商品分得的价值才能决定其价格。对于这种关系,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只有转型后的价值才能决定价格。比如人的价格——工资,同样劳动一个月,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是50元,但是现在是5000元。不仅如此,北上广深的工资就比武汉长沙高,欧美的工资就比我国高,我国的工资比印度高。这些差距的背后都得用价值分配(价值转型)的相关原理才能讲清楚。这不外是不同群体的人均财富量不同,从而其人均工资不同。劳动时间只是人们分得财富多少的一种尺度,而非它本身就是价值。
通过对工资的这种简单对比分析,我们能意识到《资本论》中的不足,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二卷中的举例,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因为《资本论》一二卷中说的价值还没有转型,没有分配,是依照“谁创造归谁”这个原则来剖析的。显然,价值转型理论说的是另一番景象,即A商品的价值中有一部分转移到别的商品中去了,构成别的商品价格的一部分。
实际中,粮食、木材、房子等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只在于发展快的部门创造的价值转移过来了。发展快的部门生产的商品,由于它们的价值转走了一部分,所以它们的价格是下降的。这样,站在群体(国家、地区)范围内看,这种上涨和下降在总量上正好相等,从而物价水平不变。这就是实际中总是强调稳定物价的理论原因。
正是因为有价值分配(价值转型)的存在,所以我们得先研究价值理论,再谈价格理论。这就是说价值理论不是多余的,不是练脑的。比如35年来我国粮食的价格从 011元/斤 涨到现在的2.2元/斤,一旦离开价值分配理论,用其它任何价格理论(含效用价值论)都没法解释。比如用供求理论解释,难道我国现在的粮食比35年前更供不应求?比如用效用理论解释,难道是粮食现在效用比35年以前大些,更饱肚子些?
在不同商品价格间的这种你涨我降的这种互动关系中,工资总是不断上涨的,这只因为我们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不给人们多发钱——即涨工资,多生产的商品卖给谁?
显然,虽然正比律在我国马克思价值理论学派中得到公认,但是我国学界并没有找到工资不断上涨的原因。
总之,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是质与量的关系。价值与长度、重量、体积等等一样,属于量的范畴。价值就是财富的量,就是使用价值的量,这样上面一系列问题便全部化解。由此有:劳动量是人们分得社会财富(工资)的尺度,利润率是企业分得社会财富的尺度,税率是政府分得社会财富的尺度。任何群体(国家、省市等)的总财富都是依照这三个方面分割完毕。
(五)价值的计量单位是什么?
中测量商品多少的尺度是货币,我国规定的计量单位是“元或者圆”,采用十进制。但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中没有研究货币,对此“以足值金银”一笔带过。依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除以单位金属货币的价值量就等于单位商品的价格,于是将价值的计量单位消隐了。因此,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对于我们看见的价格而言,无关紧要。所以我国的学术界对价值的计量单位也漠不关心,从而丧失从量纲角度去检测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长处和短处的机会,这对我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价值理论不是一件好事。
《资本论》中这段原文如下:然则,它的价值量要如何去测量,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测量。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劳动时间又用一定时间部分,例如小时、日等等去测量。
从现代的计量和测量知识看,马克思这段话就是逻辑不顺,语法不通。理由如下:
其一,前面得出“价值”这个概念时没有使用排除法,以排除非劳动品一定不是商品。比如某人捡到一颗天然钻石,那么这颗钻石的价值该怎么计算?以此类推,天然的土地、石油、天然气、树木等等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出卖?这一系列问题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没有办法消弭,理由是劳动力不是将劳动对象转化成商品的唯一原因,二者的覆盖范围不一致。没有自然力量的参与,我们一件商品都不能生产出来,没有商品何来价值?
那么问题出在那儿?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二卷中分析是依照“谁创造归谁”这个理进行的,从而有“因为价值是工人创造的,所以价值都要分给工人”这个判断式。这个判断式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根。如果我们从“人类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终端消费”这个理上进行论证,就很自然的将价值转型植入到《资本论》第一卷中去了,论证要简洁很多,流畅很多。
那么,“谁创造归谁”与“人类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终端消费”有什么区别呢?我国早期有“不劳者不得食”的提法,这是列宁依照《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最先提出的。我国现在完全抛弃这种提法,相反对一些好吃懒做、残疾、长期病痛等等人也会给一定的人道救助。显然,这种人道救助与“人类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终端消费”这个总原则相一致,与“谁创造归谁”不一致。
其二,“然则,它的价值量要如何去测量,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测量”是结论直出,没有任何论证。这段话与更前面的陈述明显冲突。这段陈述是“所以,此等物不过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会有人类劳动力支出,有人类劳动积累着,当做它们同有的社会实体结晶,它们便是价值——商品价值。”。从汉语角度看,积累着的人类劳动不就是劳动量吗?依此就有:价值量就是劳动量,劳动量就是价值量。这样说用劳动量测量价值,岂不是说自己测量自己?毫无疑问自己测量自己有多少是不可能事件,比如自己的身高当尺子测量自己有多高,怎么进行?
其三,依照马克思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证,我们利用微积分很快就能得出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以劳动时间这个数学公式,即q=ft。
马克思没有对“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进行必须的数学解析,以排除劳动中的主导因素——劳动力与劳动量无关。毫无疑问,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与“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测量”明显有冲突,而与q=ft这公式十分吻合。依照q=ft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认为复杂劳动中支出的劳动力大些,所以有倍加关系,而非马克思说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倍加关系。
总之,《资本论》中有三大缺陷,一是对测量和计量知识储备有不足,由此导致其价值这个概念含糊不清;二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没有建立价值分配理论——即价值转型理论,导致《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与实际脱节;三是对数学知识储备不足,不足以支撑《资本论》中所必须的数学分析。
总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是劳动时间价值理论,是半个劳动价值论。另半个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力价值理论,它被马克思平均掉了。这种失误由两个原因共同导致:一是在于马克思在对懒惰和勤快的分析中有明显失误,没有看到懒惰在劳动时出工不出力,支出的劳动力小些,从而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懒惰生产的商品少些,因此他不可能占勤快的便宜。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可能由懒惰和勤快的对比分析引申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二是采用平均分析法时,平均值一定要平均常数k表达出来,而非让其消失。显然懒惰的平均常数k比勤快小些,低职称的平均常数k比高职称的小些。
劳动力才是劳动的内核,内核不在何谓劳动?正确的做法是直接对q=ft这个公式进行平均运算,这需要一定的微积分知识作支撑。马克思可能不具备这种知识,所以直接将劳动力平均掉,不予考虑。总之,真正的劳动价值论一定是劳动力价值论+劳动时间价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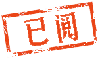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victory][victory]。
[victory][victory]。 [titter][titter]
[titter][titter]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