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永久军事经济理论(上)
作者:[西班牙贡萨罗·波索 著 王维平 夏淼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10年夏季号刊登了西班牙学者贡萨罗·波索题为《永久军事经济》的文章。文章通过回顾战后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开支的理论研究史,论述了军事开支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同时也力图对资本主义战后繁荣和70年代以来危机的原因以及国家干预的演变史作出解释。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早在1938年,列昂·托洛茨基曾在他的《过渡纲领》(题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预言,苏联将面临垮台,西方资本主义也同样将面临一次危机。然而,战后的世界景观就算没有与托洛茨基的预测完全相反,也是大相径庭。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其两百年历史中为期最长、上涨最快的经济扩张时期:迈克·基德荣(Michael Kidron)曾在1970年写道:“高就业率、快速经济增长和稳定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从整体上看,1950——1964年期间经济系统的运转速度是1913——1950年的两倍。”
上世纪40到70年代美国的经济翻了三倍。西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翻了五翻,并且在相同的时期内,法国的经济增长了四倍。较之于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末,“甚至惨淡、长期下滑的英国经济也增长了一倍”。西方被“美好”时光笼罩之时,苏联不但顽强地屹立着,事实上在纳粹德国被摧毁以后,它扩大并巩固了对东欧的控制。
在饱受第四国际组织和政治缺陷的折磨之外,托洛茨基主义陷入了理论混乱之中。除托洛茨基主义以外,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使很多左翼人士深信,自由民主制(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影响国家的能力)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国家扩大总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和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为基础)的结合,可以在商业周期繁荣与衰退的摇摆中创造一条通道,开创一个全新持久的繁荣期。
上世纪70年代初特别是1973年以后,经济增长骤停,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全球危机,其特点是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即所谓的滞胀)。那些旗帜鲜明地拥护凯恩斯主义并在60年代末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流声音的人们,在此刻遭到了冷落。与之相似,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他们身处无法解释的繁荣和出人意料的萧条的两难困境中,两者出现的时间和持续直接否定了他们的分析和预测。
对于许多最初就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左派人士来说,迟到(约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总比错误好。他们猜想,也许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意味着托洛茨基一直都是正确的?比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就持这种观点,他曾在1979年论证,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其预言的时间而非其逻辑。但是无论这种思想上的180度大转变所提供的安慰多么具有诱惑力,最终,正如克利斯·哈曼所说:“由于每个人知道马克思的危机理论30年来都无法解释这个现实世界,即使它现在突然奏效,也不能使所有人都轻易地认为这一理论一直都是正确的。”
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凯恩斯左派的双重困境突出了一个理论的失败:无法对战后经济的繁荣做出实际的解释,就无法对危机做出清晰的解释,并且也无法对任何派别的社会主义给予分析性指导。
除了前所未有的GDP增长水平和微不足道的失业率,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还进一步出现了两个具有较大历史新奇性的特征:一是国家对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庞大武器开销。在一战结束后10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欧洲国家就立即开始重整军备。尤其在1933年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后,武器支出突然增加,迫使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入了一种“从萧条到战争”的狂热轨迹。虽然在这段时期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本性和一战以来工业、通讯和交通领域内的技术发展本应会极大地加速经济从下滑坠入崩溃,但是二战之后的军事花费(在1945年后一度迅速下降)从50年代开始猛涨,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军事开销增长最为迅猛的美国,在整个50到70年代,其军事负担一直在GDP的9%左右徘徊。在英国和法国,军事负担分别从5.1%和5.5%增长到6.5%。一份充分的战后资本主义分析报告将不得不包含对这些因素的说明。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分析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平稳快速地增长。而这个事实对于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德·沙德(Ed Sard)和英国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持相似的观点。尽管他们论述的内容和范围有重大区别,但二人都试图对战后资本主义做出明确有效的经济分析,这种分析是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计划同样也能够避免前面提到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出发点(并且根据这些出发点,资本主义存在着能合理地被管理以保持稳定并长久持续下去的假象)。最终,这样的一个计划应该是那些改变冷战期间体系的历史事件之间诚实对话的结果,因此这种计划能够避免一些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墨守成规的分析。他们顽固地认为资本主义将走向“立即的崩溃”或者已取得“永久繁荣”的突破。
这种传承是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能够发展的基础,自那时起,这一理论与克利夫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偏移不断革命理论一起,已经成为本刊的政治传统的中心原则之一。随之而来的第一个目标即是通过追踪溯源来研究这一理论的构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国际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党的前身)所发展的对军事经济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一些通过和凯恩斯主义及战后资本主义需求不足理论长期对话演变而来的见解。
军事凯恩斯主义
随着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尤其在1939年二战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开始得到广泛的关注。二战本身似乎就是经济干预的优势和使用公共支出作为一种保障经济增长和高就业率方法的最好证明。在二战期间,凯恩斯确实受到了国家财政部门管理者们的重视。凯恩斯本人注意到了军事支出的短期经济利益,但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们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会转移生产要素,并且起不到有用的社会作用(当然除了自我防御)。正如凯恩斯所哀叹的:“从政治上来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要组织起所需规模的开支来做实验,以证明我的理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在战争状态。”
军事支出一度被看作是应对经济萧条的灵丹妙药,它代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种腐败,当它被国防部门官员利用时,便模糊了凯恩斯在需求管理方面更好或更坏使用的原始界限。正如杰出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迈克尔·卡莱茨基从30年代中期就一直观察到的,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在国家不与个人资本相竞争的经济领域的总需求方面加大了优势作用。此外,鉴于军事支出的直接优势,比如资源能更容易地分配给国防有关部门,断言军事主义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种挪用导致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谈及军事凯恩斯主义时便将其视为“杂牌凯恩斯主义”的最坏烙印:“正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者说服继任的总统们说,财政赤字没有任何害处,听任军事工业综合体利用它,结果让凯恩斯宜人的白日梦变为了恐怖的噩梦。”
凯恩斯主义也开始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分析。甚至在二战前匈牙利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于1939年写的《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就已经提出德国重整军备的经济问题。瓦尔加是莫斯科世界经济研究院的领导,并于1939年进入苏联科学研究院。他指出了军事主义在德国的有益的效果(卡莱茨基也曾关注过),使德国的总需求增长到失业几乎“消失”的程度。
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点的一个类似结合体现在保罗·斯威齐在其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中对军事经济的评论中。作为美国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军国主义上升“到永久且稳步增长的重要性地位”会带来三个后果。他所强调的第一个结果是“在那些像钢铁和轮船制造业等对军备生产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享有特权的垄断”阶级的兴起。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特殊的关系,意味着军事主义通过为他们确保大量的订单和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出口,使他们的巨额利润再投资,从而为垄断资本家带来好处。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能够抵消资本主义体系消费不足的趋势(也就是生产的商品价值不能够完全在市场上得到实现的趋势)。按照保罗·斯威齐的分析,军事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有这种功能,是因为军事支出和其他种类的消费支出没有什么不同。第三个重要结果是军事支出对整个资产阶级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通过它,国家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需求(并且打开市场)。
斯威齐的最初观点在1966年和他的朋友保罗·巴兰合著的一系列文章(题名为《垄断资本》)中,得以提炼和升华。巴兰也是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事实上,《垄断资本》里的关键概念之一——“总经济剩余”(即社会生产出的价值和生产这些价值的成本之差),在理论上较之于马克思所理解的剩余价值更接近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指标器。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大的经济财团和公司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操控西方资本主义。
由于这些经济体特殊的内部结构(主要是它们的规模和它们在市场上面临较小的竞争),使它们能够顺利地持续争取更低的生产成本,同时保持它们产品相对较高的市场价格。结果,垄断资本主义就倾向于生产过高的总剩余,这会比通过正常消费或投资就能够吸收的经济水平增长得更快。经济该如何应对逐渐加大的消费不足的压力?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广告(也就是他们号称的“促销手段”),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公共福利供给来增加国家支出。但对于斯威齐和巴兰来说,总剩余最重要的出路是军事支出,因为公司反动的政治意识导致军事主义而非社会项目成为了优先选择。
通过垄断资本理论,斯威齐和巴兰能够为在这一阶段被普遍认可的事情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即没有军备开销,美国经济会很容易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状态。他们坚称,美国战后经济的增长应直接归因于自战争以来的高水平武器支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的深度低迷和50年代的相对繁荣之间的差别,完全可以用50年代大量的军事支出来说明。”
然而,专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及其政策制定者一方与另一方的斯威齐和巴兰之间有意思的区别,在于后者不相信“通过军事预算的无限制的扩张可以保证经济永久繁荣的假象”。首先,正如帝国主义经典理论所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含有不稳定性和国际冲突的因子。第二,如他们所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部门的资本正变得越来越集中,这一特性会大大减少军事部门对就业的潜在好处。(值得关注的是,斯威齐和巴兰并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反抗可能给他们描述的体系强加一个极限:更有可能的是,垄断资本的政治终结可能是外围革命性断裂的结果。)
《垄断资本》的理论抱负与其经验依据的相对缺乏之间稍微有点反差。如果斯威齐和巴兰是正确的,那么军事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就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作为国家收入一部分的军事开销就越大。创造总剩余产品的能力越大,就会导致更高程度的消费不足,反过来,这就必须由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尤其是军事支出来抵消。进而,军事经济的范围越广,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就会越快。这在经验上能适用吗?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希斯曼斯基(Albert Szymanski)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去证实这些言论的有效性,他比较了1950——1968年间1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就业率、公共支出水平和军事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比率。他的结论是复杂的。总的来说,他找不到高收入国家将它们一大部分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花费在军事经济上的证据。(主要的例外有美国和英国。前者是一个高军事支出的高收入国家,后者的军事水平与其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不成比例。)
其次,希斯曼斯基无法证实斯威齐和巴兰关于高水平的防御支出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虽然他确实找到了更高的公共支出通常会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证据。这些复杂的结论并不能对《垄断资本》的普遍观点形成驳斥。相反,希斯曼斯基断定,这些结果意味着斯威齐和巴兰将军事经济作为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主要途径的论断是错误的。接着他又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垄断资本主义比斯威齐和巴兰让我们相信的要复杂得多。”换句话说,斯威齐和巴兰并没能使垄断资本主义与作为更高水平福利支出对立面的军事支出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
斯威齐和巴伦第二个十分具有理论意义的论点是军事开支的角色,即其作为解决消费不足的方法,进而成为经济衰退和危机的解决方法。这可能意味着统治阶级或是其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部门明白并追求军事开支的经济效果。假如这样的话,也可能表现出,军事开销的波动起伏或多或少地对应着整体经济的起伏波动(也就是说,军事开支的增长伴随着GDP或就业率的下降)。
两个争议都将再次出现在基德荣和哈曼发展的永久军事经济理论中,所以我们将会在后面进一步探讨它们。现在我们转入对二战后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内部的发展历程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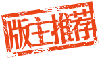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