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3月到1987年7月,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
在省长任上,王郁昭先后与两位省委书记搭档。同时上任的省委书记黄璜,是新进的省委常委,也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省委书记时四十六岁,比王郁昭年轻十岁。他原来是县委书记,提拔为地委副书记后即进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学习尚未结束时即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在原来的班子方案中,他是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这种不拘一格的官员任用,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那时,官员提拔的台阶尚未形成,越级提拔很常见。现在,这种提拔的台阶次序是很清晰的,比如不担任同级副职则一般不能担任正职;位置之间的移动轨迹也是基本清晰的,比如虽然是同级,一般先担任副省长才能担任副书记,或者先担任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再担任常委副省长。黄璜担任省委书记三年,因为受到省委秘书长案件的影响,被调任江西省副省长。随后,调来了新的省委书记李贵鲜。李书记原来是辽宁省委书记,也是一个年轻的省委领导。在谈到与两位省委书记的配合时,王郁昭说,不论是黄璜书记,还是李贵鲜书记,他们相处得都很好,个人间彼此尊重,工作上积极配合。
尽管王郁昭认为与省委书记合作很好,但是,在安徽省内省外,关于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还是有不少议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郁昭调任北京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议论,说他在省里很强势。有一次,我随一位副部长到安徽调研,晚上一位农口负责人请吃饭,席间谈到了省长王郁昭。他说,在安徽,省委书记的批示往往被有关厅局长压住不办,要等省长王郁昭的批示来了以后再定怎么处理。现在,王郁昭聊天时,时常谈到二十几年前当省长时的陈年旧事,我曾问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不知道。即便有,也不说明我和书记关系不好。但是,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一个厅局长在接到省长或书记的批示时如何处理,要考虑很多因素。”王郁昭从来不认为自己与省委书记关系不好,不因为自己资历深、情况熟,就对省委书记不尊重。他说,那时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排位靠后,他的压力很大,工作特别努力。
关于王郁昭在省长任内的表现,社会评说自然不会一致。但总体上,他被认为是一个敢负责、有魄力的省长。特别是,在他离开安徽二十几年以后,省里上下议论到这些年的领导,不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常言说,做事和做官并不是一回事,善做官者未必能做事,能做事者未必善做官。在现代政治环境中,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党委和政府的混合领导是现在体制的重要特点,但是,不论从建政之初说起,还是从改革以来说起,党委和政府之间的领导功能界定,虽然原则上可以说明,实际上混沌不清。就运行机制来说,党委和政府的分工其实并不清晰,党政两个主要领导之间远未形成制度化职权配置格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为官,其中是非成败,不论本人或外人都殊难分说。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整党刚刚结束,文革中的表现仍然是领导干部考察的首要因素。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但是,为什么这样旧事重提的举报能够再起波澜,而且构成巨大杀伤,似乎很难理解。小举报终成大气候,是需要条件的,问题的背后想象空间很大。一般来说,此类事情的背后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过往的官场积怨、当下的权力纷争、上层背景的嬗变等等因素共同作用,终于使过去的小事演绎为现在的大事。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中纪委谈话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不久,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我也听到不少说法,但对此事有较多了解,则是源于1991年秋天的一次出差。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一队人马在南方考察农业工作,随行的有五六位副部长,还有几个省的副省长,王郁昭也参加这次了考察。五六天的行程中,有在农村的实地考察,也有座谈会,晚上则往往是休闲放松的安排,如酒吧闲聊、打牌或者打球等。我从一些茶余饭后的议论中有所领悟,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涉及十几个人的系列调动,既包括一些省的领导人,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的领导人。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他是王郁昭的好朋友,考察期间常有聚谈。这些调动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一些相当层次的官员,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高层政坛的剧变也直接影响到部门和地方。个中情势可谓玄机深重,不仅外界人士难以明察,即便这些被调动的当事人,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也往往不明就里,甚或一知半解。至于笔者本人,因为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更不敢妄作解人。官员谱系的演变机制或者说运作逻辑,也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因为公开透明的竞争性选举无足轻重,封闭的内部博弈则显得纷纭复杂和迷糊朦胧。要窥探和展示其中机理,委实困难重重。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研究的艰辛所在。
谈到当年的调离,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后来,我若有所悟。纪检行动根本上是政治过程,而非法律过程。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是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的遭际常常使我陷入迷惑。在中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何其复杂,“法治”往往成为政治之一部分。一方面,官员被处理是因为违纪违法,违法和被处理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实生活中违法违纪者甚众,且官员变质并非一日之功,有关部门也非完全闭目塞听,但是,是否查办、如何惩处,则取决于政治的考量,而非法律的严格沿用。法治承认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本身是确定的,文本清晰、程序明确、标准统一,司法过程不过是技术性过程。但是,政治过程则是不确定的,区敌划友,形格势禁,较量博弈几无定则。用卡尔·施米特的话来说,政治无非就是处理极端的冲突以确立秩序,但是如果任何冲突都需要纳入政治过程,那么政治也就被湮灭在无尽的琐碎之中,而无法真正去面对根本性问题;所以,人们需要不断地将已经在政治中成熟的规则通过法律、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再有类似的问题就直接依照现有的法律或者行政规范加以处理。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治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或者不使用,那么法律自身的权威将无法自立。在一些现实的案例中,被惩处者往往忏悔“跟错了人”,而不是“做错了事”,似乎暗示了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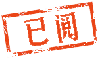

 雷达卡
雷达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